 |
 |
 |
 |
2018年对重庆市歌剧院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歌剧《尘埃落定》的曲终奏雅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无比自豪、激动。该剧由编剧冯必烈、冯柏铭,作曲孟卫东,导演廖向红等一批“重量级”的艺术家合力打造,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担任主演。重庆首演后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各界人士观看后都难掩内心的激动,真挚表扬的同时也提出中肯建议,主创人员在不断修改完善中追求精益求精。最终,这部反映时代的歌剧于2019年3月17日、18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两场。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众多艺术表现中歌剧被认为是叙事功能较弱的一种艺术形式,要在不足两小时的时长中把原著超30万字的剧情描述充分演绎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这也成为了创作这部歌剧巨大的困难之一。阿来通过十二个章节描绘了高原最后一个吐司的没落,而歌剧则用了四幕来呈现了一个旧世界的本末终始。这一切,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手法是难以完成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西北音乐可谓是最具民族标识了,新疆、西藏亦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风格最独立、极具辨识度的。如果简单的用音乐分析中双四度音程框架显然是苍白、孱弱的。《尘埃落定》的音乐是藏族的,丰富的、是多变的、是厚重的,拥有了这些维度,它便是“国际”的。
《尘埃落定》讲述了社会底层的奴隶命运的解放,以藏族音乐为基因,用“二少爷”真、善、美的戏剧角色,奠定了歌剧基调占据先机。作曲家以民族音乐为主线,在调式的运用、运用独唱、合唱、重唱等演唱形式、在配器等作曲手段中悄无声息的溶于西方作曲特点,使其丰满而厚重。当“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如歌、如吟、如诗、如画,蝶儿摇曳了花香,摇曳了花香,是谁在把谁,把谁牵挂……”的男女二重唱想起,已经奠定了歌剧的音乐的主导思想。甜美、有扬,作曲家反复用上行五度、下行回归的手法,选择带有鲜明藏民族风格的带清角的五声调式,将这段名为“情话”的二重唱写的缠绵、纯洁。
 |
 |
 |
谈该歌剧的民族性不仅从音乐创作的本身出发,表演者的舞台呈现是最直接的传递着,演员通过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直接传递给观众。“二少爷”是该剧的重点,剧组选择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来担纲这一角色并非仅看重歌唱家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他长期的西北生活经历,以及其在演绎西北音乐作品的准确、独到的艺术造诣。作为我国本土培养的歌唱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咬字、唱腔以及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是得天独厚的。有专家曾说“没有去过国外就唱不好美声”,在此并不评论其观点是否存在局限,但从文化感受力上至少解释了艺术家创作作品式不可或缺的主观体验。当第一幕中藏族音乐的标志性唱词“呀啦哩嗦”响起时,扑面而来的藏族味道让每位观众深信不疑。
该剧音乐鲜明的藏族风格是不可质疑的。但主创全剧并没有选择一位原生态歌手来增加其民族性,全体演员除了王宏伟其余演唱人员全是经过长期西方美声唱法训练并活跃在美声届的歌唱家。这在当下的歌剧中并不鲜见,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中国歌剧要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探索,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下,让中国声乐作品插上翅膀飞向国际大舞台仿佛成了当代声乐艺术家的的理想。更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自信。
歌剧研究学者居其宏教授在观看完该歌剧后评论:“我认为《尘埃落定》这个戏有希望打造成新时代民族歌剧的⾼峰”。 作曲家王祖皆说“这是一部具有整体艺术美的歌剧。这部戏作为剧作家为音乐写戏,作曲家为戏写音乐,是一个范本。这是一部可以向建国70周年献上厚礼的歌剧作品。”还有全国很多艺术评论家、导演、编剧等认为该剧是“一部登上民族歌剧之舟,更傲立船头的作品。”
歌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从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演员舞台调度的视觉呈现到乐队的演奏、演员的演唱、台词等都是构成歌剧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各个环节的相互平衡中彰显了导演的创作能力和意志。《尘埃落定》的呈现是和谐的,这样的和谐并非全是共性中的整齐,而是在反差中找到更高的平衡。如写实的舞台设计和诗意的音乐相和谐。舞美设计在舞台上几乎原貌呈现了坚实、厚重的“官寨”,在强烈写实的布景中,男主角演唱了“问天、问地、问神明,问山、问水、问大海,为何奴隶的女儿就是奴隶,为何主人的儿子就是主宰”突出这位尊贵二少爷对下人的怜悯,使得主角的伤感、悲愤、绝望、昏乱与现实贵族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人物内心矛盾。该剧很好的运用了藏族舞蹈元素,但并没有使用专业舞蹈演员,而是由合唱队员兼任,提供了载歌载舞的场面。达到视听的完美结合。
《尘埃落定》不仅在歌、舞、乐上达成了统一和谐,同时也运用了多媒体的虚实结合。剧中“复仇者”的三次出场都是一袭黑色披风,与之相配设计了“火”的场面。火是以黄色与红色为主色的,黄色和红色与黑色在24色相上都是相距度数最高的,对比色度数越高视网膜对其辨识度越到,到达的生理冲击就越大,导演以这样的方式渲染了紧张、强烈的复仇气氛,强有力的推动了戏剧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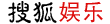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