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查明哲 资料图 |
查明哲的导师陈顒对他说:你身上具有不是能够“学”来的东西,那就是激情与执着。
他的“激情与执着”来自于对人,对人民的热爱。
走向人民的导演美学追求
“戏剧就是教堂”——这是查明哲的苏联博士导师对他说的,而查明哲从中悟到的是戏剧艺术是人的艺术,是解析、挖掘人的灵魂深厚内蕴的艺术。
于是,他在戏中解析和挖掘人的灵魂的同时,热情地发现人的灵魂宝匣中珍藏的火花,热情地雕塑人的灵魂的具象。在《立秋》中,这灵魂的火花就是马洪翰的母亲龙头拐杖上的那串钥匙:当她抛出钥匙,拿出珍藏了十三代窖藏金子的时候,灵魂燃烧了;在《矸子山》中,这灵魂的火花就是男女主人公跨越生死界限的婚礼;在《万世根本》中,这灵魂的火花就是18条汉子按红手印时的烛光;在《我那呼兰河》中,这灵魂的火花就是那条从天而降的呼兰河,它弯弯曲曲,千回百转,却终究不改向前奔突的方向;在《老大》中,这灵魂的火花就是国良苦苦怀恋着的乡亲与爱人,大海的涛声与灯塔的光芒……
在发现、点燃舞台人物灵魂火花的同时,查明哲也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观众——当《立秋》结尾的舞台上落下一片叶子的时候,那是导演(他和他的老师陈顒)的灵魂在拍打着丰润厚实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呼唤着不久就要到来的“立春”;当《矸子山》的秦大咧咧跑出一条大斜线,在矸子山的顶端,向心爱的女工喊出“我稀罕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听到了查明哲的喊声,喊出了他对承受苦难,跨越苦难,征服苦难的主人公们诚挚的爱;当《万世根本》的七代花鼓女唱出凄婉的民间小调时,我们也仿佛看到了查明哲在“叹息肠内热”,仿佛看到了他在向着多难的民族伸出了拥抱的双臂;当《我那呼兰河》的全体主人公在生命的河流中奔波奋斗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查明哲全身沸腾着呼兰河的怒涛;当《老大》的主人公国良呼喊着,发誓要“把鱼找回来”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查明哲正在拉着观众的手去探寻命运的奥秘……
这就是雨果所说的:“走出学府,走出教会选举会,走出套间,走出小的爱好,走出小的艺术,走出小的教堂……”文学的目的是“人民,人民,就是人。”
在人的困惑中探寻其中蕴涵着的宝藏
查明哲聆听到了时代的呼唤——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核心理念。它同时也应该成为话剧艺术家们所尊崇信奉的理念。查明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在走向这样以人为本的新型社会中,人的命运,人的品格,人的内心世界,必将发生着重大的甚至是激烈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出现巨大的调整,在趋向大和谐的总过程中,必然发生前所未有的心灵冲撞。而新道德,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也必然伴随着过去的陈旧的梦魇般的顽强纠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命运将更加诡谲,也更加丰富多彩,为话剧舞台提供更丰厚、更深刻、更异彩纷呈的内容。
在《矸子山》和《万世根本》中,我们看到的心灵撞击,其本源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在新时期的大调整——凤奶奶对田专员的发问以及田专员勇敢地为民撑腰;秦大咧咧的艰苦汇报以及他作为党的干部把善意的谎言与严峻现实对接的艰难过程,都显示着这种人际关系大调整的目标——官为民而生,官为民所用。
在《老大》里,充满着对20世纪百姓生活的审视和反思,对社会与人,自然(大海)与人,命运与人的交织糅合,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着伤感而又无奈的回味,梳理,批判,怀恋……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混沌,唯有一个梦,犹如出海的明月一般朗朗地升腾起来……这个梦就是人与世界的和谐。
斯泰恩在分析《推销员之死》的时候说,主人公威利-洛曼揭破了社会成功的法则……而观众的反应并不需要询问“后来怎么样了和为什么”,重要的是要他们觉得,“噢,上帝,的确是这样啊!”而查明哲的现实主义不仅要让观众认同“的确是这样”,更要和观众一同去探寻在“这样”的背后丰富厚重而又诡谲多变的蕴涵。譬如,《老大》中的国良,他真诚地尊重阿龙伯、老鬼叔和老鬼的年轻遗孀阿兰,然而,他们却都因他而死去;他无比眷恋着大海和家乡渔村,然而,他和渔民们一生的勤劳却使子孙们无鱼可打,渔村变浴场,灯塔变瓦砾。他凭借执着的爱,投身灵魂的故乡——大海,变作像人一样的鱼,探寻着……
所谓“00后现实主义”的本质,或许就在这里。
没有门户之见的导演风格
查明哲用自己的激情与执着沉静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承袭导师陈顒的风格:大气磅礴与激越恢宏。而在导演美学上,他又宗师于徐晓钟先生的表现与再现的融合。当他还是学子时,就闪现出了“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宽阔目光,“咬定青山不放松”地开拓着艰难而明确的征程。没有门户之见正是学者导演应有的风范。
查明哲寻找现实主义的再现与非现实主义的表现相融合的道路,是否表明他对现实主义的怀疑和动摇?不,恰恰相反,这正表明了他坚信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吸收与融合来自外界的合理因素,以壮大自己,发展自己。那么,他为什么要追求对非现实主义再现的融合呢?表现主义最初是在绘画中产生的,用凡·高的话来说,就是“强有力地把自己表现出来”。赫尔曼·巴尔在1916年说过,这是“灵魂发出的尖叫”。查明哲注重“灵魂发出的尖叫”,包括他的舞台呈现。《死无葬身之地》中尖利的刺耳的枪声,《纪念碑》中斯科特高高举起那块顽石,《青春禁忌游戏》中轰然倒塌的门,《万世根本》中家瑞听到妻子腹内孕儿的躁动,大吼一声……不都是灵魂在“尖叫”吗?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演员的创造力和观众的想象力中,一种明澈的火焰便被激发并燃烧起来了”(梅耶荷德语)。其实,查明哲所融合的“表现”不仅来自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还有来自象征主义(例如《纪念碑》中冉冉升起的少女裙衣),来自结构主义(《死无葬身之地》的铁架布景)等等的某些元素为现实主义所用。他不仅在师从方面,在创作方法上也处处体现了“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宽阔视角。正如斯泰恩所说:“实际上,要想找到一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戏剧或纯粹的象征主义戏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那些最杰出的戏剧家在风格上总是丰富多彩的。”
导演的才华是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查明哲苦心孤诣地寻找形式的过程,也就是加深对“内容”(精神)的认识的过程。《立秋》中,高墙深院,鳞次栉比的屋脊,完美得不容丝毫变动,隐喻着悲剧产生的根源;《矸子山》那高耸的煤石山预示着主人公们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终将攀登的境界;《万世根本》那占据舞台五分之四空间的黄土转台开宗明义地揭示出人与土地这个“根本”;《我那呼兰河》那千回百转的河流象征着苦难的人们终要奔突汇向民族解放的洪流;《老大》则把整个舞台变成了渔船,从船桅到船板,从船头到水下,转换自如,全剧就是在无垠的大海之上游荡,在现今与过往之间寻找,从容自在。其间,尘世如海,人生如船的况味咀嚼不尽。
这就是刘勰所说的“神用象通”。这里的“象”,就是有意味的直觉加深体现思想精神的艺术形式,这样的艺术形式是玩味不尽的。这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我们可能会一千次地遇见一个普通感觉经验的对象而却从未‘看见’它的形式……正是艺术弥补了这个缺陷。”查明哲就是这样的“发现者”,所以,他是新世纪“杰出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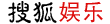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